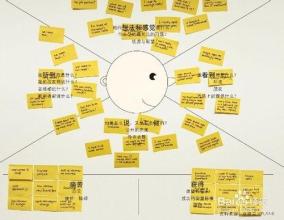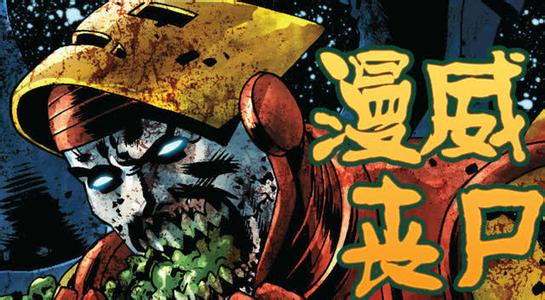系列专题:《亲历神秘外交背后的16人:中国高端访问10》
也许是风雨如磐年代里的苦难生活,凌青和几位兄长、姐姐都毫无例外地选择了革命道路。回忆起那段历史,凌青说:“虽然作为林则徐的后人,但家庭对我们思想教育方面的直接影响并不大,对我们影响大的应该说是那个时代,我上初中时正赶上‘一二?九’运动,我和那个时代所有的热血青年一样,都因亲历日本人的残酷统治而具备反抗思想。” 高中时,凌青在北京四中上学,平时喜欢读书。课内书读得不多,课外书倒是读得不少。像巴金的《家》、《春》、《秋》和鲁迅的一些著作,就是那时读的。当时正是日寇占领北平时期,对进步书籍查得很严,凌青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哥哥林曾同和他的一些同学经常想办法带一些书籍回来,其中就有不少进步书籍。“当时我们担心日本人找麻烦,每次把那些进步书籍看完后就埋在地下。我最初就是这样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书籍的。” 1941年,凌青进入北平燕京大学经济系学习。当时燕京大学有个学生进步组织,叫Three Reading Club(意为“三个年级学生组成的读书会”),读书会的会长是凌青的同在燕京大学读书的二姐林锦双(后来改名傅秀),解放后在地质矿产部工作),实际上读书会的组织者是燕京大学的大四学生、地下党员赵凤章和陆孝华(解放后曾任湖南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凌青当时参加了读书会,在赵凤章和陆孝华的介绍下,凌青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这里,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最初启蒙,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等大量进步书籍。 太平洋战争爆发的1941年12月8日深夜,日本人强行封闭燕京大学。不幸的是,“学生读书会”成员名单为日伪警方所侦获,旋即大肆搜捕进步学生。犹如惊弓之鸟的凌青夤夜潜至友人家蛰伏,待风声过后于同年底转入北京大学经济系就读。 但是,偌大的北平城终因日寇侵凌践踏,再也无法为年轻学子凌青安放下一张平静的书桌。1942年7月,凌青从家里出来后转移到北平一个地下党员家中住了20多天。后来组织上安排凌青和其他一些学生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去,当时组织上安排的路线是从北平东便门车站坐火车到保定,在事先约好的旅馆住下来,组织上再派人带他们去根据地。 到了保定后,凌青住在约定的旅馆里,半夜日本宪兵又在街道上盘查,气氛挺紧张的。过了几天,组织上派人把凌青接走,趁日本宪兵检查的空隙出了保定城,越过游击区,找到交通员后又摸黑穿过敌人封锁线,走了一夜,第二天早上赶到了聂荣臻领导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晋察冀分局组织部长刘仁(解放后任北京市委副书记)热情接待了他们。组织上安顿好凌青后,要求凌青不要再使用原名林墨卿,以免让在北平的父亲、哥哥因为他而受连累。凌青思索一番后,遂将林墨卿改为凌青。 凌青说自己姓名的改法有讲究,之所以把姓从林改为凌,一是当时自己思想比较激进,将姓改为凌,象征着跟封建家庭背景决裂,彻底革命;二是因为日本人没抓住自己,“凌空而去”,来到根据地。至于改名,则因为原名墨卿中的“卿”与改名中的“青”谐音。自此之后到现在,凌青之名一直沿用至今。 在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敌工部当了两年干事后,凌青就来到了日夜向往的革命圣地延安,那是1944年初夏,抗战胜利已见曙光…… 学者大使坚定站在第三世界一边 1971年,外交部正在就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紧锣密鼓地做准备工作,凌青也参加了这一中国外交史上的重大活动。1972年,以黄镇为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了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这是中国在恢复联合国席位后参加的第一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凌青参加了这次会议,主要处理前方联合国文件。 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被恢复以后,凌青曾多次出席多种国际会议。当年,香港和澳门是否属于殖民地的问题,摆在了联合国非殖民化委员会的面前。时任外交部国际条约法律司副司长的凌青参与有关部门香港、澳门定性问题的讨论和拟稿。中国政府关于殖民地概念以及香港、澳门的准确表述第一次出现在国际讲坛:殖民地是遭受外国统治管辖而丧失主权的国家,香港、澳门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国家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结果。香港和澳门是英国和葡萄牙当局占领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完全是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根本不属于通常的所谓“殖民地”范畴。中国政府主张,在条件成熟时,用适当的方式和平解决香港、澳门问题……联合国无权讨论这一问题。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