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周日的早晨,我在一种很寂静的状态下醒来。关掉闹铃和手机。空气里暗藏着一些静止的繁忙,闲适和喧嚣骤然隐匿。光洁的白瓷花瓶里,百合依旧。思索着,今天,是该怎样忙碌的日子。
2011年9月,我正式升入了高三,与此同时,我也接到了一份特别的任务——组织创办二十中的首期校刊。
校刊,是我的一场旧梦。那得从很久前的往事说起,太过琐碎,不便唠叨。
往事和现实之间始终隔着时空的距离。人便是唯一的焊接者,不断地将记忆拼凑,整合,或者再拆散,支离破碎,粘贴和复制。如一部古老的无声黑白电影,那些思想在清疏的空气中激烈地对白,直至人的内心异常惊恐,而后顺着枝蔓将一些无关痛痒的细节处理,割舍,摒弃。
保存的,终是最珍贵的美好。
校刊之于我,便是如此。
记得高一的一个明媚的下午,我曾经那样大言不惭的跟我的同桌说过,我要办校刊!为此,我那位可爱的同桌还特地把他初中的校刊拿给我看。
可惜啊,这或许只是一场旧梦,一如秋风锁住了光阴的真相,冬雪收藏那些朴素的段落,安静如初。一如我带着期待的心情加入了团委学生会校刊部,看当时的部长把校刊的工作一拖再拖,拖到他毕业,拖到我高三,或许就此,不了了之。
直到那个下午,刘晨曦老师找到我,给了我一道简单的选择题:校刊的工作,接或者不接。萨特说:当一个人行动的时候,他就是在做选择,一种自由的选择。或许从高一我加入校刊部起,我的选择就已经注定了。如此说来,是不是应该说我很有勇气?
兴奋么?有点儿,仅仅一点儿而已。之后便是心慌。
据说,我们的学校是有过校刊的,只可惜,它的无疾而终留给我们的经验只是一个零。突如其来而无从下手的工作让我感到莫名的心慌,当然,不止我,还有我的副主编,我的编辑们。每次例会,我很笃定的告诉他们,没问题的,咱一点点的干就好。
可其实,我有着同样的惶恐和不安。高三了,我还在为校刊的事奔波着,忙碌着,花掉本就不多的休息时间,我真的开始犹豫是不是从一开始接下这份工作就是个错误。只不过,作为背负着“主编”名号的我已经没有了选择退却的权利,将征稿通知发下去的那一刻,也就注定了我不再拥有说放弃的资格。
如果目标是正无穷,那么我们或许可以不那么在乎起点是零,还是几百几千。四个月,我就是带着这样的信念,完成我校刊的工作的。
从零开始,从零出发。
从第一次开例会面对那些陌生面孔我的手足无措、语无伦次,从第一次的征稿的一无所获,从面对出版社提出的要求我听得云里雾里,从编辑们一次次的询问,学校领导老师一次次的催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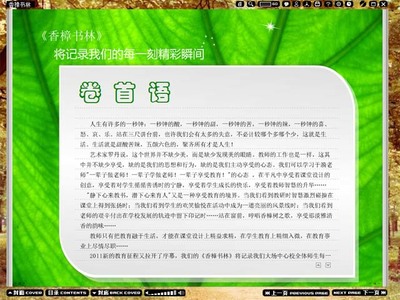
到今天,我,和我所带领的编辑部的同学们完成了这次的校刊工作。四个月。
这不是二十校刊最完美的样子,这离我们最初的设想差了很多,非常抱歉的说,有很多工作我没有做完,不得已,只能把一些栏目删减、合并。
但这真真正正是二十中校刊的一个开始,万事开头难,第一步,我们迈出来了。
这是一个忙碌而寒冷的冬天,我带着我可爱的校刊,大抵是熬过来了。
只记得十八世纪那个英国诗人笃定的呐喊:
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我在等待春天的来临,含笑不语,不惊不动。
我们的校刊名是我起的,叫《艾拾》——少艾年华,纸笔拾年。
少艾年华,且行且唱,一段似水流年中最美好的唤作青春的时光。那青春的案头,任意一张肆意纷飞的旧画面,都是落落年华中揉碎的精彩剪影。
纸笔拾年,当似水流年稀释了粘稠的往事,铺陈在纸上的流光碎影却依旧清晰,我们或许应该感谢手中的笔,悄然拾取起这些最美好的华年。
北京市二十中学,校刊《艾拾》以此得名。
愿你,同《艾拾》一起,拾取美好,珍存年华。
如我。一个恋旧的人,喜欢在松弛的光阴里紧紧攥住一些故事,念念不忘,生生不息。
也许今生成不了谁胸口的那颗殷红的朱砂,我也要珍藏这些美丽的痂。
偶尔,也喜欢放肆。喜欢胡言呓语,与时光揽杯换觥,拟欲酣醉。
欢迎 新浪微博 @纸绎
 爱华网
爱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