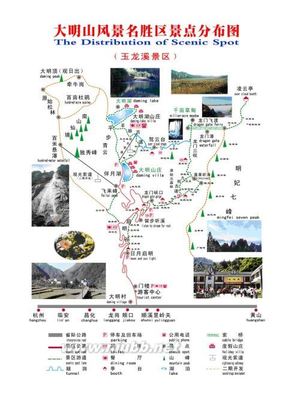每年的这个季节,都听到朋友到京都大阪赏红叶的消息。看他们发在微信上的图片,心被勾得又痒起来。因为,因为,去年的高野山之行,眼前也是一片枫红啊。记得从高野山回来,又去了深圳。在忙完一切正事之后,我把自己关在宾馆里写这篇文章,那样的迫切而又郑重其事,在我还真是第一次。一方面,是为了不辜负约稿的杂志,更重要一面,是为了不辜负高野山的一寺一塔、一树一石。
在怀念的季节贴上旧文,但愿还有一天,重访高野山。
“虚往实归”,还是想从这句话说起。虽然初学日语,知道日语句子中的汉字,并不都做汉字理解,但第一次看到空海大师手书的名句,还是对着其间的汉字,像公案一样参了参。想要知道,我即将造访的高野山,那千年前从中国修法归来的空海大师,要留下怎样的信息给后人。
公元804年11月,也是我到他的高野山的季节,三十岁的空海一路乘船,从福州登陆,前往长安。“星发星宿晨昏兼行”,既是他旅途疾行的写照,也是他决意求法心情的映显。抵达长安时,已经是十二月二十三。次年5月,他访青龙寺,首次进谒佛教真言宗第七代教主惠果高僧,六月即受胎藏法灌顶,七月上旬,受金刚界灌顶……作为一个留学僧,中国的长安可谓他的福地,他在这里精进佛法,抄写经书,同时研究中国的诗词格律。806年,在他返回日本时,身份已经是真言宗第八代传人。他带回的佛经宝物,现在只有有缘人,才能在他所创建的高野山一睹。也有部分,藏至京都。不仅对于日本,对于人类,这些都是重要文化财。
佛教的魅力超越国界,所以,惠果大师尽管中国弟子上千,还是传法给他认为最该传之人,没有人埋怨他偏心,反而要感谢,从此,唐密变东密,一段中日文化交流的佳话就此写下。也从此,青龙寺,高野山,有了心的牵系,跨越时空,直至今天。而对我来说,亲切感还来自于,他学法的青龙寺,恰好在我的家乡。想,那时如果他修法有闲暇,会不会一日看尽长安花?空海大师还是位诗人,他曾写下一本有关中国诗词格律的研究著作《文镜秘府论》,当年若在中国以诗会友,所吟诵出来的诗句,可是我所熟悉的秦音秦调?
非常好奇,还在于,出生在四国的空海,为什么执意要选高野山作为他的修持传教之地;以“密”闻名的高野山,究竟有多少可以“显”给我们?说来,一直喜欢禅宗的我,一时还不知,以怎样的心情进入它,才能与它相应。
种种的思虑、揣测与期待,真正在踏入高野山时,突然放下,说来这还是一辆列车的启示。
天空号,向天界驶去
“天空号”是一趟通向高野山终途的绿皮火车,样子方方正正,人进得车厢,座椅除两端的四人小包厢外,一律朝窗,仿佛就是让你专注于外面的风景。座位紧俏,需要预定才有,所以真正上下站的人并不多。如果没有工作人员在车厢间走动,外面的人看这一列车厢的人,就是一部默片。人人眼神专注,像在做一种仪式。日本是有仪式感的国度,所以也便默认,“天空号”如此布局,就是把看风景变成一种仪式。人在仪式里通常静默,心也会因此趋向安静。渐渐也会觉出,这趟列车的本质就是“空”字,车窗也不过取景框而已,人面对一闪而过的绝美风景,不把自己完全放空,就无法把外面的风景全部纳进来。
但这样说也是另一种徒然。因为在行进的车中,用相机捕捉风景,多数都不成功。想要拍眼前的枫红,相机里出现的是一抹烟霞。想要拿赤红的柿子去馋人,留在镜头里的则是一串串红灯笼。美到极致就成绝望,越留恋就越抓不住,索性停下拍照,只就是个看。看这山峦叠嶂中,到底哪一座山才叫高野山。想,既然坐的是天空号,会不会随它一路向天界驶去。
山门其实也令我惊异。别的山门一入,便是寺庙。而高野山的山门更像个界标,告诉你,穿过去,就是高野山的世界。这个世界有伽蓝,也有市役所、警察局、便利店与小饭馆,有僧侣的面孔,也有过着世俗生活的普通人。看着车子在路上穿行,不同的人各司其职在工作,突然觉得这就是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小镇。空海曾说:“以佛眼观之,佛与众生同住解脱之床,无此无彼,无二平等。”也许,这名为高野山的方圆六公里,至今不把尘世和寺院严格区隔开来,就是这个原因吧。
当然,这只能算作初踏高野山的我,对空海所说的佛理的一种粗浅理解,就像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高野山也同样不是。在下午的参观中,我们就看到了正在修建的中门。空海活着的时代,他被天皇敕赐此地,但当时的高野山还寂寂无名,少人居住。空海从公元819年着手建立高野山,直到入定,这里的一切还是未完成时。今天的规模,有赖于后续弟子不断在建,同时还有部分属于毁坏重建。高野山寺院,木制结构众多,地势又高,碰上雷电火灾,总有些地方难以幸免。所以建了毁,毁了建,也是常事。不过重建也有重建的好处,一些新的避雷设施,或者先进的防震技术便可以增加进去。现在参与中门建设的,是建造过东京塔的。因为信赖他们的技术,这里的僧人告诉我们说,这个中门建起来,两三百年应该没问题。许多的大殿外观,看来是木质的,里面已经运用上了钢铁结构,但一些有传统印迹的设施,仍然被保留。比如作为高野山寺中之寺的金刚峰寺,就能看到屋脊上的一对水桶。为我们讲解的僧人告诉我们,用它防火灾,是江户时代寺院的发明。
无量光院的土生川正贤住持
这些年经常也会去各处的寺庙里参观,但高野山最具代表性的根本大塔的颜色还是让我稍有些奇怪,是通体的桔红色。后来知道它也有色彩的过渡。上面的九轮不算,中间的黄白赤黑青五色,分别相配于地水火风空这五大。塔本身是大日如来的象征。诸佛中的大日如来,是密宗至高无上的本尊,和空海之间,有一段特殊因缘:话说当年,惠果大师为空海灌顶,曾蒙其眼,让他执花投向曼荼罗。曼荼罗处处有佛,但神奇的是,空海两次投掷,花都落在大日如来这边。大日如来别名遍照金刚,所以,惠果为空海取名遍照金刚。在高野山,“南无法师遍照金刚”,意思就是“皈依空海大师”。
把高野山的历史与传说讲清楚给我的,是无量光院的住持土生川正贤先生。土生川正贤先生是地道的高野山人。算得上纯正的僧侣世家。父亲曾为金刚峰寺住持,但对孩子的教育很特别。很小的时候,父亲便把他送到别的寺院受教育,担心在自家容易娇纵。土生川正贤先生高中与大学,是在大阪读的。而且都跟佛学无关。“你应该看看别的世界。光学佛学就狭隘了。”这是父亲的想法。所以在外国语大学学完了中文,土生川正贤先生便又来到了广东的中山大学,学了七年中国哲学,等于和老庄思想打了七年交道。但回日本高野山,他又做了密宗和尚。
一个看够了外面世界的人,出家难道没有犹豫吗?小心地将这个问题抛出,土生川正贤先生马上接碴:有啊。有的。“那时很想当大学教师,师傅说——他依旧习惯称父亲为师傅——两条路可以同时进行。于是我就这么做了。”现在,土生川先生还在高野山大学教中文课程。
虽然佛教的密宗教理复杂又玄奥,基本不示人,土生川先生还是用通俗易懂的八个字概括了真言宗的要义:上求菩提,下化众生。“有些佛教徒专心于佛法的精进是可以的,但和外界交流,解除众生烦恼同样重要。”土生川先生有自己的FACEBOOK,为的就是和众生互动。但这也带来一些烦恼,他说随顺众生就难免犯戒,这里面总有些尺度需要拿捏。
日本的僧侣在外界看来可娶妻生子,仿佛已经戒律很宽,但从土生川先生这里,可以知道这同样是误读。不同的宗派尺度不同,但认真的僧侣,心中还是有持戒的观念,所以即使是因下化众生而触戒,也会心不得安。
高野山,心安即为家
人能弘法,法不远人。和高野山的真正亲近,应该说,始自于能和土生川先生用中文顺畅交流的这一刻。我由此知道,当年惠果大师把两部大经《大日经》、《金刚顶经》传给空海,而在世称东密的真言宗中,空海又把这两部不同的经变成不二的整体。
空海为什么选中高野山作传法基地,因为他年轻时曾造访过这里,这里原是山连着山,八峰林立,但并没有一座山,明确叫做高野山。空海觉其八峰像八瓣莲花的形状,便在它的中心,一个相对的平展之地,建起了高野山。都说“天下名山僧占多”,在这里,恰好是反着的。有空海才有高野山,因为是他“发现”了它,并且依此映现出佛法的奥义:莲花在污泥中不染绽放,这也喻示着,人可以在污染的世界,有一颗清净的心。每个人心中都有佛的种子,端看自己是否觉悟。
要建一个从中国传来的真言宗的佛教寺院,还要争取周围住民的帮助。空海大师的做法是,首先建起神社。随顺众生,方能应缘,因此,作为坛上伽蓝而存在的建筑群中,会出现神社,就不算奇怪了。
虽然对前人的教义有重新的梳理,但是青龙寺作为祖庭的地位,在高野山人心中自始至终没有改变。土生川先生记得青龙寺现在的住持叫宽旭法师,他自己也经常与西安的密教寺院交流密切。如今的西安已经不是古长安,我问他会不会有些失望,他说:不会啊。虽然现在也有大厦高楼,但晚上抬头望月,还是觉得那是空海大师曾经看过的月亮。
高野山是一个完备的世界,有幼儿园、小学、中学与大学。如果土生川正贤先生从来没有离开过高野山,最后做了无量光院的住持,我也觉得是能理解的。但他其实又不是,可以算做走了很远的路,最后又回到起点。不过,这里的僧侣也是众生相,有人离开又返回,也有人,万里迢迢来到高野山,反认他乡为故乡。
到高野山第二天,看僧人上早课,我就发现了这么一位。
高野山的六时钟,每天只响两次。一次是早上六点,一次是晚上五点。六点是所有僧侣到本堂做早课的时间,我们一行的幸运是,土生川先生允许我们观看:就坐在后排的椅子上,也可以坐在地板上,地板有暖气的。
那天的早课,作为住持的土生川先生并没有做领诵,他要在左侧一个空间做护摩。“护摩”就是为他人祈愿的仪式,念经中还有烧火这个环节。烧火供天是做外护摩,而它真正的深意是将自己的内心点起来,将有烦恼的众生内心的杂质烧掉。
右边的僧侣齐诵《理趣经》,并伴着长长调子的梵语声明。《理趣经》是不能向外人传授的经,因为里面有怕人引起误读的部分。我在吟诵的僧众中看到两位外国面孔,心下好奇,没想到早课完毕,进到一个说话的房间,竟然就看到其中一位,在和我们中的一些人吃茶聊天。
他是德国人,生着一张英俊成熟的面孔,来高野山修行已经十一年,通日语、德语,但不通中文。借助毛丹青翻译,我问他为何会来高野山,他说了很有意思的话:有一年我在福冈,听到天空传来一个声音,空海大师对我说:以高野山去吧。然后我就来了。
他说,这里就是我的故乡。

这个德国人,听到了一声召唤,从此,把高野山当成了自己永久的家……
神带路,生死桥
奥之院,听土生川正贤先生讲解它的一切
高野山的密宗和尚,要经过一个非常严格的100天苦行,早上两三点起床,持咒念佛,学很多很多东西。还有一项是,身体坐在冰冷的水里持咒。这个考验人求法意志的水池,就在奥之院。
奥之院是我们离别高野山前最后造访之处,也是我此行最难忘的地方。奥即深奥之意,也是最接近空海的地方,只要你走过三座桥,空海就在佛国那头等着你。
有土生川先生一路陪伴讲解,这一切理解起来容易得多。此时的他,已换上一身暗绸花纹的僧服,他说这一件更正式。高野山的僧侣的僧服上,胸前的轮袈裟,是五层折叠的。他说这里有讲头。释迦牟尼悟道期间,把所有的衣服都送给了别人,身上仅有的衣服便只能缝缝补补,折叠起来穿。所以轮袈裟也要显出折叠与缝线的痕迹。用文艺一点的说法,这是向释迦牟尼致敬。另外不能忽视的,还有上面印着的家纹。高野山的寺院有百来十个,各自都和历史上幕府大名有联系。有的是得到其供养,有的是为他们解除过烦恼。土生川先生的轮袈裟上,同时印着上杉谦信家与广岛的浅野家的家纹,表明他所主持的两院,和这两个大名有关系。
奥之院杉木参天,很多都是上百年的古木。空气浸凉,阳光透过树隙照下来,已变成光影的游戏。一条长长的石板路,长约两公里。起步就是第一桥。人先要合十行礼,因为迈出脚的第一步,就意味着从俗世界到了神圣界。路两边都是墓,大大小小几十万。说来高野山,生者三千,逝者上万,生者没有逝者多。
林间有乌鸦叫,脚下有土生川先生的木屐声。我问他,乌鸦在日本人心中,到底是怎样的形象?他说,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出现不吉利,另一种是神带路。
我对他说,我愿意是后者。因为这一路越往后走,越带有启示意味。比如,墓碑上的名字,很多都是日本历史上的重要人物。武田信玄与上杉谦信生前是死对头,死后的墓却隔路相望。能够和不共戴天的敌人平安相处,可以说是生死化解了一切。同样的,丰臣秀吉曾经派兵攻击过高野山,高野山的和尚去和他谈判,他被和尚一席话折服,转而又来保护高野山。所以他的墓也在这里。令人惊讶的倒是,这里同样能看到日本净土真宗的创立人亲鸾上人的墓,甚至还有俳圣松尾芭蕉的句碑。松尾芭蕉生前曾来过高野山几次,1694年,51岁的松尾芭蕉去世于旅途上,他曾写下俳句:途中正卧病,梦绕荒野行。不知为什么后人不把他葬在这里,而只是为他立一个句碑。
没有尊卑,没有敌我,甚至不分宗教信仰,有意愿就可以葬于此,这当然这是高野山的胸怀,但从我们外来者看来,土地还是有限的,将来不够了怎么办?土生川先生的态度是,先走着看。我想他隐含的意思其实是,佛菩萨总是有办法的吧。
还有人为动物立碑。我在这里看到两处,就是医学机构为做实验的小动物所立的墓所。众生平等、敬畏生命,在这里有目共睹,已不是一句口号。
一些小小的墓碑像上,有人为他们戴上了脖套,仿佛是怕他们寒冷一般。生者用自己的感受体味逝者,这一份温馨挚情,高野山的僧人也用到了空海身上。奥之院有空海的墓园,就在桥的那一头。这里称之为“御庙”。因为空海的信徒们始终相信,他们的宗师还和他们活在一起。
所以每天凌晨四点,会有一队僧人,送水供他洗脸。早、中午两次,为他送饭。过午不食,但也奉茶。季节变化,或有重要仪式时,要为他更衣。冬天则要为他开暖气,夏天则要想着为他纳凉。
空海大师是3月21日往生佛国的,所以每月的21日也是他的重要纪念日。我们参观奥之院这一天,恰好也是21号,所以时时能看到前来拜空海的信徒、寺院僧与高野山不同年级的学生。有一行人身份最特殊,他们一律身穿白衣,背部竖行印着“南无法师遍照金刚”字样。旁边还有几个字:同行二人。
土生川先生解释说:这些人叫遍路士。他们从四国空海大师的家乡出发,要把与空海大师有关的88个寺庙都拜访一遍,行程一千二百公里,历经三十多天,最后才到高野山,与空海大师打个招呼。白衣是为逝者而穿,因为沿途餐风露宿,非常艰苦,若有人倒下,他们则可以一起为他做仪式。白衣上所印“同行二人”,并不是指一起出发有二人,而是指与空海大师同行。他们的心中,始终有一个活着的空海大师。
同样,从中桥跨上第三道桥,走向空海的御庙,许多信徒也相信,空海大师并不在这个御庙中,而是活在丛林中。所以他们一般都从御庙穿行到后面,面向这片丛林,虔诚地颂经祈愿。
踏上第二道桥,就算是到了死界。沿途看到最多的是地藏菩萨。死界的人都是无缘升入佛国的,所以地藏菩萨要为他们代受苦。到达第三道桥,前面就是佛国。所以这第三道桥,在我看来最为特别。它由三十六座条石组成,每一条石背面都刻着一个佛的名字。而整座桥,又组成一个佛,共37个,正好是金刚界的37佛。人踩在条石上,看来对佛有些不敬,但也喻示着,是佛在渡我们到佛国去。
拜完御庙,一般要从原路返回,再经历一次佛国向俗世的转换,也等于把那些日本历史人物相关的历史事件,又重温了一遍。一去一返,缭绕于周围的,始终就是高野山寺庙特有的线香,头顶乌鸦的鸣叫,以及土生川先生木屐踏在石板路上的声音。神奇的还有,一点儿没有感到被墓园环绕的恐惧。
作为宗教名山,高野山对香的运用最为特别。一般寺院都是烧香,高野山寺院却讲究进得庙门手上先涂香。临别时,我在一家纪念品商店特意买到了这种香。因为记得空海大师《遍照发挥性灵集》中有一句:“持香身自馥,洗衣足自净。”香其实也是一种虚与实的存在,但却是最恒久的记忆。我想我会在遥远的某日,燃起一炷香,回想我在高野山的一切。
是离开后才想起,忘了请教土生川先生,空海大师手书的那句话“虚往实归”,在信徒那里做什么解。网上当然不乏对它的解释,但我还是觉得,佛门中人,解释起来更地道。
没有留他的电话,只好短信请教一位也曾修过密、来过高野山的禅者,他回了几个字:密教中以假修真之意。(孙小宁写于高野山归来,刊于2013年《知日》杂志)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