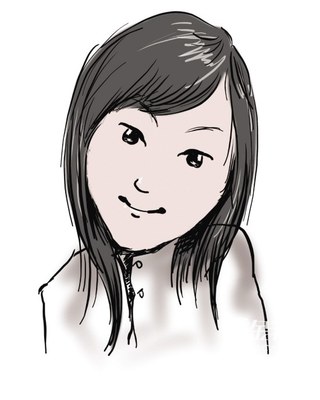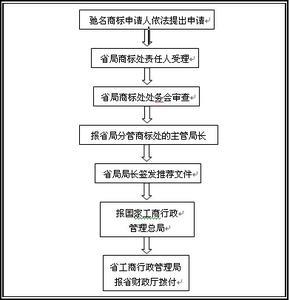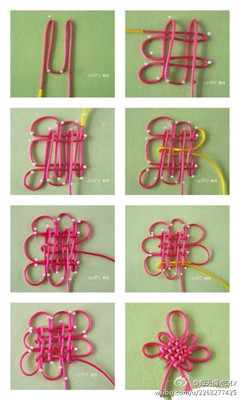如何欣赏中国书法
一、书 法 欣 赏
我们常说:“艺术是没有国界的。”也就是说,不管什么艺术形式,任何国家、任何民族的艺术家都可以参与它的创作;也不管什么形式的艺术作品,任何国家、任何民族的人民群众都可以参与它的欣赏。大体上,这样的认识当然是不错的,但唯独书法,稍稍有些例外。真正能从事书法创作并称得上书法家的,似乎主要是中国人,而真正能够欣赏书法艺术的,订是的似乎也还是中国人。当然,日本、韩国的书法创作和欣赏也很当行出色,但它,正是从中国的书法渊源而来,属于“本是同根生”的同一种艺术。
诚然,包括书法在内,艺术都是属于形象思维,因而不受国界、民族、评议诸葛亮因素的限制。所谓“耳之于声有同听,目之于色有同美”,“天下之耳相似也,天下之目相似也”,关键在于有没有能够欣赏音乐的耳朵,有没有能够欣赏美术的眼睛。但是,书法却与其他的艺术有所不同,它所塑造的形象,是中国独有的汉字;用以塑这样的形象的“语言”,是中国所独有的笔墨。这就使得其他国界、其他民族的人士,在欣赏时可能产生障碍。
在这里,需要附带谈谈书法艺术的性质问题。作为造型艺术,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所谓“形象”,列非是具体的物象,又称“具象”,或不可名状的物象,又称“抽象”。据此,有人认为书法是“抽象艺术”。其实,这样的观点并不确切。因为,书法的形象并不是“不可名状”的点、线、面、,而是非常“具体”的一个个汉字的点、线、面。所以,确切地说,它是“汉字”的造型艺术。但是,一般书写的汉字,计算机打印出来的汉字,并不能成为书法艺术,是因为它他都没有经过对汉粽子进行造型的笔墨处理,就像植物学的挂图、动物学的挂图,作为“标本”,没有经过造型的笔墨处理,也就不能称之为中国画艺术、绘画艺术。正如在中国画中,形象的塑造为大前提,笔墨的组织为小前提,同理,在书法艺术中,汉字库的塑造为大前提,笔墨的组织为小前提。只有汉字,没有笔墨,不能称为书法;只有笔墨,没有汉字,也不能称为书法。前者,只有一般的书写,甚至计算机的打印;后者,则成了真正的抽象艺术,如今的“现代书法”、“浒书法”、“前卫书法”之美。
有人会说,欧美国家,不是也有很多人士爱好中国书法吗?其中,尽管还没有真正能称得上是书法家的,但怎么能说他们之中就没有真正懂得欣赏书汉的人呢?显然,这是因为对“欣赏”两字的理解不同。
诚然,根据所谓“接受美学”的观点,欣赏是充分自由的,所以,“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事实上,这样的“自由”还不是真正的“充分”。因为,“这一千个读者”所得的“一千个”印象,毕竟还是“哈姆雷特”,而不可能是“奥赛罗”。其中,哪怕只有一个读者是,他的“欣赏”所得到的印象,不是“哈姆雷特”而是“奥赛罗”,他就算不上是能够欣赏《哈姆雷特》的读者。
“看到骆驼,说是马背肿了”,固然也可以算是一种对骆驼的“欣赏”,但本书所要讨论的书法欣赏,是不承认这样的“欣赏”的,因为它还没有“入门”。
真正的欣赏,它既是自由的,又是不自由的。不自由的,是关于所欣赏的艺术的基本常识,如哈姆雷特就是哈姆雷特,而不可能是奥赛罗,骆驼就是骆驼,而不可能是马。在这不自由的基本常识的框架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它又是自由的,有一千个读者,就不会只有一个哈姆雷特。如果只有一个哈姆雷特,它就不是艺术的欣赏,而成了数学的题的解答了。
所以,我认为干能够欣赏书法艺术的,主要是中国人。因为欣赏书法艺术的一些基本常识,倚官仗势和形式的,精神的和技术的,人品的和书品的等,从入门的要求来说,相比于绘画、雕塑、音乐、舞蹈等艺术形式,具有相对严格的国界限制。
当然,这只是从“主要”的方面来立论,而不是说,外国人就绝对不会懂得书法的欣赏,中国人就绝对都能懂得书法的欣赏。只要具备了一定的条件,即使是外国人,同亲友也能进入书法欣赏的殿堂,而如果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即使是中国人,也只能在书法欣赏的门外。因此,本书所要讨论的第一个问题,但是书法欣赏的条件。尽快餐国人把握它较难,但只要下工夫,同亲友也能把握;尽管中国人把握它较容易,但如果不下工夫,同亲友也不能把握。
本书所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是通过书法的欣赏,可以使欣赏者获得哪些些好处?它既是进入书法欣赏之前的动机和目的,又是结束书法欣赏之后的收获和结果。如此地循环往复,欣赏都要便在不知不觉中获得了身心的愉悦和精神的提升。
事实上,所谓“动机”也好,“目的”也好,对于艺术的欣赏,包括书法的欣赏来说都不例外。它,往往是不自觉的,不明确的,而不是如做其他的任何事情那样,是自觉的,明确的。一个人之所以会去欣赏书法,他的“动机”、“目的”主要就是爱好,就是喜欢,这种爱好、喜欢是源自内在的心理冲动,而不是出于外在的功利需要。因为有这样的爱好,所以他就会去参与欣赏的实践,把握欣赏的条例,对于书法的欣赏,由爱好而接近,由不入门而入门,由入门而登堂入室。这一过程,是在内在爱好的驱使下,在欣赏的实践中完成的。而每一次的欣赏,都歙了的爱好不断地得到和提升,这种满足和提升,便是他的“收获”和“结果”。
唐代的张彦远热衷于法书名画的欣赏,孜孜,节衣缩食,妻子僮仆笑他说:“终日为无益之事,竟何补哉?”他长叹说:“若不为无益之闪,则安能悦有涯之生?”显然,欣赏书法艺术,既不是为了谋取直接的功利,也绝不是为了消磨多余的时间精力,而主要是为了使爱好得到满足,包括使思想、境界得到提升,精神、情操得到陶冶。爱好得到了满足,有涯的“生”命的质量也就得到了提高。思想境界得到了提升,精神情操得到了陶冶,当他投入本职的工作时,也就能更加振作,做得更好。
今天,现代的物质文明截止来越丰富,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人们精神上的压力进行欣赏,无疑,可以作为我们调节身心的一种良好形式,使我们调节身心的一种良好形式,使我们虽置身于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的物质生活之中,却能超然于其上,而不至于成为物质的奴隶。
问题是,不仅仅是钢笔等硬笔代替毛笔成为书写的工具,白话诗文代替文言诗文成为国语的表达方式,而且,计算机的键盘几乎代替了一切用笔的书写,外语和拉丁文字也正在取代白语和汉字的一部分运用。今天,虽然仍然作为中国人,但由于文化背景的大变易,我们要想把握欣赏书法的基本条,也变得几乎与外国人同样有困难了。
一方面有的欣赏需要,一方面又缺乏对欣赏条件把握,这就需要我们一道来做启蒙的工作。这一工作,将不仅是每一个书法欣赏者个人的福分,同时也是整个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艺术的福分。
二、知 世 论 书
一件优秀成果书法作品,往往反映一个特定时代的精神,不仅从文字内容上的,而且从笔墨形式上。因此,对于有些作品的,了解它的时代文化背景,就显得相当重要。
当然,反过来也一样,通过对这件书法作品的欣赏,可以使我们更深刻、更形象地认识这一段历史。因此,知世论书,是书法欣赏的一个条件,而赏书知世,也是书法欣赏的一个收获。尤其是古代大量无名书工所创作的优秀作品,要对它们的艺术性有充分认识,时代背景,时代风尚,就是一个重要的依据。因此,读一点历史,对于进入书法欣赏的殿堂,是不可或缺的一课。
三代,是一个由野蛮文明过渡,充满了血与火的洗礼的时代,在攻伐、征战、残杀、祭祀中诞生的一切艺术,包括书法艺术,自然也体现了这样一种时代精神。我们今天面对那些钟鼎铭文的拓片,得到的是一种朴厚凝重,带有崇高、悲剧意味的审美印象,而要想使这样的印象深化,便不能不了解这段历史。
同样,要想真正深入地认识汉碑隶书艺术那种雄深雅健之美——庄严浑穆而又天骨开张,方整中见变化,雄强中有奇险,古拙中涵气势,我们也需要对汉代“大风起兮云飞扬”的时代精神有所认识。
礼崩乐坏之后的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同时又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的愚人节,超变虚灵的魏晋风度,使向来具有崇高目的的书法艺术,转而用于抒发心灵的闲适,于是书家各自不同的个性风格创作,汇成了晋书“尚韵”的共性时代风格。
对此,宋代的欧阳修有一段话分析得最为透彻:“余尝览魏晋以来笔墨遗迹,而想象前人这高致也。所谓法帖者,其事率皆吊候病,叙暌离、通讯向,施于家人友朋之间,不过数行而已。盖其初非用意,而逸笔余兴,淋漓挥洒,或妍或丑,百态横生,披卷发函,烂然在目,使骤见惊绝,徐而视之,其意态如无穷尽。使后世得之,以为奇玩,而想见其为人也。”所谓“想见其为人”,正是想见其人所处的那个“丧乱”且“频有[祸”的社会时代。
而当江南的士大夫对礼教的质疑转向自我的追求,即所谓“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时,北方中原的朝野,则由对人生无常的难以解脱转向对佛教的礼拜,一时盛行造像碑、墓志铭,又形成了北魏书,包括整个北朝书悲怆沉雄的风格。南帖北碑,南秀北雄,南文北武,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两大主流派别,即所谓帖学和碑学。
逮至唐代,即是继汉之后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盛世,同时相比于汉,一切典章制度也臻于成熟严密,真可谓如日中天,达到巅峰的状态。自然,在这样的历史背景、时代精神下所孕育出来的书法艺术,也就以森严的法度体现了雍穆堂皇的气象。
苏轼曾说:“知者创物,能者述焉,非一人而成也。君子之于学,百工之于技,自三代历汉至唐而备矣。故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可见唐代,尤其是盛唐时期,社会的风气所趋,不仅影响到书法艺术的成就和风格趋向,同时还整个地影响到其时包括诗、文、画在内的全部文化创造的成就和风格趋向。离开了对时代的认识,当然不可能取得对书法艺术的正确认识。所谓“笔墨当随时代”、“文章关乎气运,非由人力”,讲的都是这个意思。
崇文抑武的宋代,在军事上和对外关系上积贫积弱,老是处于屈辱退让的地位;但在国内,却因此而保持了长达数百年的稳定局势,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达,迎来了文化艺术的全面繁荣。当然,这种繁荣,主要不是体现于崇高的目的,而是于闲适的心情。欧阳修说:“学书可以消日。”这是一种的闲适心态。苏轼说作书可以发抒“一肚皮不合时宜”,这也是一种闲适的心态。只是相比于晋人超脱的闲适心态,宋人的闲适心态却并未能真正超脱。因此,同样是行书,晋书尚韵,而宋书则尚意。
此外,如明清之交,由于政治的腐败、与政权的更迭,导致社会的长期动荡,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王铎、傅山一路奇崛书风的出现,不仅有书家个性的原因,更当有社会的原因。
同样,清乾嘉之际掀起了碑学高潮。对于是这一路作品的欣赏,如果能联系到评论家狱、考扰学等等文化背景,也可以加深我们对它们的审美认识。
还有像明代的台阁体、清代的馆阁体,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书法史现象,也是由社会时代的因素所决定的。当时的科举制度,要求士人能写一手工整的小字,这样不仅便于考官阅卷,而且登仕之后,用以书写典章、典籍,也格外有用。以官场“实用”的要求,置于“艺术”的要求之上,自然也就形成了如此这般几乎千字一面的风格。俗话说,科学讲“我们”,讲“共性”,艺术讲“自我”,讲“个性”。在书法艺术中,官场的应用当然也要求强调“我们”而不是“自我”,强调“共性”而不是个性。
以上,只是简略地从历史、时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来论证“知世论书”在书法欣赏中的意义。对这些因素,如果能更具体地深入,对于欣赏也必将带来更大的收益。
此餐,所谓“知世”,我们所需要知的“世”,不限于笼统的历史、时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因素,它也可以是同一时代的其他形式的艺术,如文学、舞蹈、绘画、篆刻等等。
例如,对于汉碑隶书的欣赏,我们可以把它们与汉赋作比较;对于张旭、怀素草书的欣赏,我们可以把它们同唐代的乐舞作比较;对于宋书的欣赏,我们可以把它们同宋诗、宋词作比较;对于八大、石涛、扬州八怪的书法欣赏,我们可以把它们同他们的绘画作比较;对于赵之谦、吴昌硕书法的欣赏,除了绘画,我们还可以把它们同他们的篆刻作比较。
三、知 人 论 书
古人说:“言为心声,书为心画。”一件书法作品,无论它是具有社会的崇高目的,以共性见工也好,还是抒发自我的闲适心情,以个性见长也好,在笔墨线条的流转间,总是会出书家的秉性和心迹,从而表现为不同的审美风格。甚至同一位乙家,在不同的场全,因不同的心绪而创作的不同书法作品,从内容到形式,其审美的风格,也总是会有相应的区别。因此,对于书家,特别是那些有名的书家,如果能尽可能充分地认识他的“人”,在欣赏其创口时,必须能帮助我们更深刻地把握作品的艺术创造性之所在。
举例来说,同时“尚韵”的晋书书汉家,王羲之的作品在艺术风格上倾向于平淡流丽,而王南献之的作品,则倾向于张扬飞动。这当然可以的圆生生世世法,而“小王”用外拓的方笔法,但为什么“大王”会“选择”内而“小王”会“选择”外拓?与其产是有意识地选择以拉开上的差距,宁说是不期而然的内在秉性、个性所造成的结果。因为,通过历史观察,我们可以发现,王羲之的秉性是平淡而超脱的,不屑于争强斗胜,例如著名的“坦腹东床”的典故,便是他个性的明证。以他如些的秉性,他自然是运用内的笔法,创造了流丽的书风。而王献之的秉性,则十分好胜,包括他的父亲也常耿耿于性,每当有人批评他的书法不及父亲,他总是很不服气。以他如此的秉性,自然地,他运用了外拓的笔法,创造了张扬的书风。
又如同是“尚法”的唐代书家,也因为个性的不同产生了不同面貌的书法。欧阳询的秉性“寒寝”而“敏悟绝人”,所以其书“劲险刻厉,正称其貌”;而颜真卿的为人忠烈端严,俨然道德君子,所以其书风友强茂密,觉着雍容,凛然有庙堂气象。然而在恪守法度的时代中,也出了了张旭、怀素那样个性奔放的书家,其本身不羁的性情,发挥于书法作品上则出现放肆的狂草,杜甫形容他“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可见其为人性情不受约束,展现在书法作品串,也是相呼应的气象。
而在“尚意”的宋代四大家中,蔡襄的人品湿润,所以其书风清丽;米芾的人品奇僻,所以其书风跌宕。所谓“观其书而可以知其人”,反过来,认识了他的人,也就可以更深刻地欣赏俯他的书法作品及艺术创造性了。
在细究书法中“书如其人”的特质时,孙过庭曾经提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观点,在《书谱》中论述王羲之的作品的段落里,孙过庭写道:“(王羲之)写《乐毅》刚情多怫郁,书《画赞》则意不瑰奇,《黄庭经》则怡怪虚无,《太史箴》又给横争折,既乎《兰亭》兴集,思逸神超,私门《诫誓》,情拘志惨。”这是说同样是王羲之,尽管具有不变的秉性,但在不同的场合及状态下,当他带着这不同的情绪来创作,所完成细微的不同。若当我们欣赏这些作品时,也能够体会到这风格上的细微不同,那便可以称得上是深入书法欣赏的堂奥了。而要想深刻地知其然,当然必须知其所以然,不知其所以然,所谓的知其然必然是不够深入的。无疑,对于所谓的“知人”一词,必须有更深入的体认。
在欣赏书法作品时,“人品即书品”这个问题也与知人论书有密切的关联。如果从天赋的内在秉性来认识“人品”,“人品即书品”的观点无疑是准确的。但如果以后天的道德标准来认识“人品”,“人品即书品”的观点则很容易出现偏颇的情形。而根据这偏颇的“人品书品”观,又导致了“应使书以人传,不可人以书传”的观点,强调书家应有高尚的道德操守,这无疑也有它的道理,但是非要从“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进而变本加厉成为“政治标准唯一,艺术标准不要”,那问题就不仅仅是偏颇,而简直是把欣赏导入了误区。
长期以来,正是由于这偏颇的“人品书品”观、“书以人传”观,导致了书法品评上的某些矛盾,在此也有必要加以厘清。
例如北宋的蔡京,据称他原与苏轼、黄庭坚、米芾并称“宋四家”,但因为为人奸佞,所以后人将他从“家”中除名,而以耿直的蔡襄取代了代在书史上的位置。然而就书法成就而言,蔡襄人为“宋四家”之一,并不仅仅是因为其风骨高洁而导致作品“书以人传”,而是因为蔡襄的书法确实极具功力,在复古风行的北宋初年,极富古雅淳厚之美,深得当时文人的赞美,从而使他“书以人传”。蔡京被从“四家”中除名,也并不完全是因为他人品低劣,而是因为他的书法确实不如“四家”从艺术水准上来看,不仅不如“苏黄米”,恐怕也只能落入李建中、欧阳修等人之流。
元代的赵孟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赵孟是宋代皇室后裔,却接受了元朝的招安,其人品志节颇受时人的讥评,从“书以人传”的观点来看,人品即已不高,书品当然也不会好,所以,后世有人直他的书法是“匪人”的“奴书”,“气骨全元”。但从书法史的角度而言,他的书法成就之高,直入晋唐,并影响元明两代以至21世纪的无数书家。从非政治的角度来看,元初赵孟被尊为艺坛祭酒,引领一时风骚。对于异民族统治之下的南方文人而言,赵孟的出仕与其说是一种民族情结的矛盾, 宁说是他对于艺术生命的妥协。
再如明、清的张瑞图、王铎,一个附从阉党,一个投降清廷,均曾被作为人品败坏的典型,为士林所不齿。依据“人品即书品”的解释,他们当然是写不出优秀的书法作品来的;但事实上王铎、张瑞图却是明末清初浪漫派书家的领袖人物,他们放纵恣肆而奇异诡序的书法风格,不但在当时书坛独具一格,在当代仍旧是众人争相临摹的对象。他们书品与人品之间的关系,绝非用二元论可以简单地加以批判的。
那么,“人品”与“书品”的关系到底又是怎样的呢?判断的关键,首先应该是如何来理解书法欣赏中“人品”的本质;其次,才能深入地探讨二者的关系;而后“书以人传”和“人以书传”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首先,“人品即书品”,或“书品即人品”确实是不争的观念。然而,艺术品评中所说的“人品”,仅是指某一个人的先天秉性,与后天的道德无关。“书品”,则是指其书法的风格,人品温和的,书品自然不会偏激,人品敦厚的,书品也不至于浮薄。
其次,艺术上所说“高”的人品,主要并不是指道德上的“善”,而是指秉性上的“大”。大奸大恶和大慈大悲,根据道德的标准,天差地别,根据秉性的标准,恰可并驾齐驱。所以,气节上有缺陷的书家,如前面举出的赵孟、张瑞图、王铎等人,因其艺术气度上有着“大”的秉性,发挥在书法创作上,也可以达到很高的成就。对他们,我们既不能因其气节有亏而否定他们的书法,也不能因其书艺卓绝而视他们为完人。
再次,一个书法家,固然需要具备高尚的道德修养,但他既然作为书家,对作品而言,就“应使人以书传,不可书以人传”。举例来说,史可法,书法成就平平,但因其为志节之士,所以世间有人爱惜他的书法,使其书得以流传,这是“书以人传”的典型;而欧阳询,在历史上并没有什么志节崇高的事迹称道,只是因书艺卓绝而扬名千古,这正是“人以书传”的典范。那么,从书法欣赏而不是道德表彰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推崇欧呢,还是推崇史呢?
也许有人会说,王羲之、颜真卿等,不都是“书以人传”吗?固然,他们的才华、学识、诗文或志节、操守、忠义,都是过人之处,但他们在书法史上之所以名垂千秋,却不完全是因为这些才华、学识、诗文、志节、操守、忠义,而因他他们杰出的书艺。否则的话,在他们的时代,如陶渊明的诗文超过王羲之,魏微的忠义亦不亚于颜直卿,这些人肯定也是用毛笔写字的,以他们如此可传之人,他们的书,为什么没有因人而传下来呢?
对于书汉的流传而言,人品的高尚当然足以造成“书以人传”,但我们也明白首先上的人品与书法上的品格并非绝对的相关。其实,各行各业,不管从事什么工作,首要的都是必须做好“人”。那么,怎样才算做好“人”了呢?首先,当然是人所从事的是什么工作,就应该安心于钻研这一工作,做好这一工作。同理,作为书法家,做好“人”的标准,首先当然应该是钻研书法,致力于写好书法。
所以,所谓“知人论书”,所要知的“人”,主要是指他先天的秉性气质,是内敛的还是外向的、婉约的还是豪放的,等等,至于后天熏陶而成的道德贞操方面的则是其次。先天的秉性就像一个人的血型、基因,各不相同却没有好坏之分;后天的道德之形成却有种种原因,尤其当遇到不可抗拒的突发性原因,善恶之分不过一念之差。此外,善还是恶,在于同的时间、地点各有不同的评价标准。古人有云:“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若使当时身便死,千古忠佞有谁知?”这说明对一个人的道德品质很容易发生错误的认识,历而道德认知有时候并不足以作为真正的“知人”。
四、内 容 的 形 式
任何艺术作品,都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书法艺术当然也不例外。那么,对于一件书法作品,什么是它的“内容”?什么是它的“形式”?二者又是怎样的一种“统一”关系呢?
通常,如王羲之的《兰亭序》、颜真卿的《祭侄稿》,其诗文被看做“内容”,所以又称“文字内容”,而其笔法、笔势、笔意刚被看做“形式”,所以又称“笔墨形式”。对形式的注意通常是为了使内容的表达更加完美准确,所以,《兰亭序》的文字是优美的,朗润的,它的形式也是优雅的,清丽的,如果用奔放或拙重的形式,便难以表现内容的韵致。而《祭侄稿》的文字是悲怆的,慷慨的,它的形式也是激越的,冲动的,如果用平和或优美的形式,便难以表现内容的崇高。
在这种情况下,形式与内容,笔墨与诗文,是一种量休裁衣的关系。对于欣赏者,要想真正认识这件“衣”的美,就不能不对穿着了这件“衣”的人“体”有所认识。古人云“言之不文,行之不远”,是指一个人的语言不美,那么他所讲的话就不会传播得太远。在古代没有印刷术的情况下,一个文人所创作的诗文,都是用书法书写了来的,从文学的角度来看,他的诗文再好,如果书法太拙劣了,读者也难免会看着不顾。对此,我们不妨认为是“文之不美,行之不远”。
大体上,从三代到两宋,对于书法的创作,多是形式配合内容。
因此,我们今天对它们的欣赏,也就应该由此着眼,透过形式其内容,因为把握了它的内容才能真正赏析它的形式。脱离了内容,单纯地欣赏它的形式,对于全部的欣赏是有欠缺的,不完整的。事实上,直到今天,读王羲之的《兰亭序》也好,颜真卿的《祭侄稿》也好,如果读的是他们的书法作品,与读计算机排印出来的文章,审美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是,对于这一期间的书法形式,如甲骨文、大篆书、草书,大多数欣赏者,根本就不认识它们,甚至于少数专家,也并不完全认识它们,如西晋陆机《平复帖》,各家就有各家的不同释文。既然字也不认识,又如何来认识它的诗文内容呢?是不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这类作品便被排除到了欣赏的范畴之外了呢?
再者,自元以后,尤其到了明清,书家的创作,大多不再是书写自撰的诗文,而是书写前人的诗文。换言之,对于前人来说,如王羲之的《兰亭序》、颜真卿的《祭侄稿》、苏轼的《黄州寒食诗》,其书法创作的冲动,乃是依据于诗文创作的冲动;而在此际,如宋克、董其昌、王铎等所反复书写的杜甫诗卷,其书法创作的冲动,并不依据于诗文创作的冲动。试问,在这种情况下,形式与内容,二者又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在欣赏中,我们应怎样来认识这种关系呢?
西方哲学家黑格尔(Hegel)在《小逻辑》中有言:“形式非他,乃内容翻转为形式;内容非他,乃形式翻转为内容。”原来,形式与内容,二者的统一关系,不仅仅表现为一种互为翻转。这样,关于第一个问题,撇开它的诗文内容,结合时代的背景、书家的秉性等等,我们可以单纯欣赏它的笔墨点线乃至通篇章法布局轻重疾徐、枯湿浓淡、疏密聚散所形成的节奏韵律。
这一切,在创作上,是配合了诗文内宾形式,在欣赏上,则已翻转成了书法作品的内容;反之,那些本为内容而为我们不认识的诗文,却翻转成了它的形式,成为笔墨所赖以表现自身节奏韵律美的依据。
进而,关于第二个问题,事实上,对于明清的书家来说,即使在创作上,也已把诗文翻转为形式,把笔墨翻转为内容了。所以,对于他们,不再是笔墨配合诗文,而是诗文配合笔墨。二者的关系,不再是量体裁衣的服装设计,而成了削足适履的时装设计。
我们知道,时装设计与通常服装设计最大的一个不同点,在于它是以衣服为中心而不是以人为中心。所以,在服装设计中,一件衣服把人打扮得更漂亮,更精神,而在时装设计中,是通过一个人(模特儿)把衣服展示得更漂亮,更精神。只要通达到这一目的,即使不用真人做模特儿,用塑料、石块、木桩、衣架等,也都无妨。所以,在明清,直到今天,书法家已很少再书写自己的诗文,而多书写古人的名诗。责骂时,在书法的笔墨风格对于诗文的文学风格的配合上,也不再以流美对应婉约,以雄强对应豪放,而往往用妩媚的书风书写古人慷慨的诗文,或用奔驰的书风书写古人深静的诗文。归根到底,是因为在这样的创作中,笔墨已经成了“内容”,而诗文则已成了“形式”,成了支撑笔墨这件衣服的衣架。
所以,对于明清书法作品的欣赏,自然也就不必太美洲它与的是什么诗文,而只要尽可能地欣赏它的笔墨便足够了。
但是,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书法的欣赏可以完全撇开文字的内容而单单关心它的笔墨形式。不仅宋以前的书法,就是明清以来的书法,无论自己创作的,还是抄录前人的,所书写的大多是一些很精美的,或具有相当历史、文化、道德、伦理、学术、艺术价值的诗文、警句,这些文字“内容”,也可以给我们充分的精神上的陶冶。例如,几百年来多少大书家反复书写过的《千字文》,便以言简意赅的文字组织,传达了非常丰富的历史、人文、天文、地理知识。所以,赏文品书,始终是书法欣赏的一个重要角度或称切入口。作为造型艺术,书法之所以既不同于“具象艺术”,又不同于“抽象艺术”,而是属于“文字艺术”,但不同于诗歌文学的“具象艺术”、“抽象艺术”笔墨的点、线、面之美,又具有文字艺术中诗歌文学的韵律、辞藻、意境之美。
事实上,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作为“文字艺术”,诗歌文学与书法本来就是而二、二而一的,既没有哪一件文学作品不是用书法书写出来的,又没有哪一件书法作品不是书写的诗歌文章。
五、技 进 乎 道
不同的艺术门类,之所以不同,主要不在于它们的内容,而在于它们的形式。例如同样一篇王羲之的《兰亭序》,或杜甫的律诗,当它们作为“文学”作品排印出来时,所使用的便是句法、语法、格律等文学的形式;当它们被王羲之本人或董其昌作为“书法”作品书写出来时,所使用的便是笔墨、点、线等书法的形式。
任何一种艺术,它所独具的技法形式,是决定这一艺术之所以是此艺术而不是彼艺术的根本所在。因此,在这一意义上,不仅对于形式翻转为内容的书法作品,我们要欣赏的重点是它的笔墨技法,而且,即使对于形式服务于内容的书法作品,我们所要欣赏的重点,在是它的笔墨技法。蝗话,我们干脆去读计算机的排字本好了,何必还要来读墨迹呢?
既然如此,可以说知世好好,知人也好,释文也好,只有真正懂得了书法艺术的笔墨技法,才算得上是狭路相逢的欣赏者。当然,对于创作,同样也是如此,只有真正掌握了书法艺术的笔墨技法,才算得上是够格的书法家。
书法的笔墨技法,大体上,可以分为笔法、结体与章法三项。笔法,是指一点一画的技法;结体,是指某一单字的构架;单法,是指通篇诗文的布局。
一、笔法
笔法,包括执笔法和运笔法。执笔法在历史演变中,实践探索中,以及因所书字形的大小、书体的不同,并不是单一的,通常最浒的为“、压、钩、格、抵”五字执笔法。这样的执笔,不仅是合于手的指腕的生理结构,而且最能使书写时的点画达到灵劝有力的效果。当然,这仅仅是众口一词了点画灵动的可能性,真正要把可能性变为实在,还需要依赖于正确的运笔法。事实上,所为的笔法,主要的正是指运笔法而言。
由于中国的汉字,有不同的点画形态,因此,配合这些点画形态的生动表现,运笔的方法也是各不相同的。笔法的典型是所谓的“永字公法”,传说王羲之攻书27年,专精于“永”P了,以其备八法之势,能通一切之字。而后世,也就把“八法”视为书法的代名词。
“永字八法”的第一笔点称为“侧”法,要求不能平其笔,而要像鸟一样翻转侧下;第二笔的起笔短横称为“勒”,要求不得卧其笔,应加如勒马之用缰;第二笔的转折而竖下称为“努”,要求矫健有力而不能直;这一笔的钩挑称为“踢”,要求畜势跃跃面出;第三笔的横担称为“策”,应如马之用鞭,仰而策之;第四笔的长撇称“掠”,应如之掠发,左出而利;第五笔的短撇称为“”,应卧笔疾掩,如鸟啄物;第六笔的捺称为“磔”,应使笔锋开张,战行而右出。
除“永字八法”之外,还有“用笔十法”、“二十四条用笔法”等等,把汉字的点画和笔法分得更加具体而微,便都没有八法来得概括。今天,则一般将笔法归纳为横、竖、点、撇、捺、钩、挑、转折八种,每一种点画的起笔、行笔、收笔(其中,钩没有单独的起笔),各有不同的要求,甚至同一种点画,因其在结字中所处的位置与上下笔画的呼应关系,也有不同的运用,如竖笔,就有出锋收笔的“悬针竖”和藏锋收笔的“垂露竖”之别。
如此,笔法虽然只有八种,实际的运用则变化万千。而且,这还只是针对楷体书来认识的。把它向简化的方向变化,可以施之于笔画繁复的篆、隶书;把它向更繁复的方向变化,又可以施之于笔画简略的行、草书。
笔法虽然变化万千,但总的共通要求,都是需要通过用笔的轻重、快慢、转折、提按、顿挫、流走,使所写出的点画,不仅仅只是构成一个个单字,组织成一局局章法,还应该赋予这些点画本身有如筋、骨、血、肉的生命,有起有止,有缓有急,有映带有回环,有虚实有偏正,有藏锋有露锋,有铺毫有翻毫,各呈生动之状,即使一点一画,皆有三转,即使一波一拂,亦有三折,如折钗股,如屋漏痕(见本丛书《颜真卿》第24页),如锥画沙,于是毫厘锋芒之间,或圆笔内而冲和含蓄,或方笔外拓而惊疾张扬,皆能沉着痛快。
笔法,也与所使用的工具、材料有关。笔有长锋,有短锋,有硬毫,有软毫;纸有生纸,有熟纸,有蜡,有绫绢;墨,有磨得枯而浓的,也有磨得饱而淡的。这些客观的因素,都能使笔法的形态和审美发生变化。
笔法,更与书家个性的禀赋密切相关。如同为“千里阵云”的一横,对于秉性平和的书家和秉性磊落的书家来说,即便同样的起笔、行笔、收笔,也必然表现为或平和、或磊落的不同风格。
二、结体
结体又称“间架结构”。因为中国的汉字,其笔画有繁多的,有稀少的;其形体,有扁的,有长的,有方的;其态势,有方正的,有偏侧的,有斜欹的。如何使这些不同笔画、不同形体、不同态势的文字,因点画的连贯穿插、分离呼应而呈现为生动的姿致,使笔画繁的看上去不嫌多,简的不嫌少;形体长的不嫌长,扁的不嫌扁;态势正的不嫌平板,斜的不嫌倾倒,便是结体的技法所要解决的问题。
汉字的结体,在篆、隶、楷、行、草的不同书体中各有不同的规律,而尤以楷书的结体,最具“楷则”的典范意义。楷书中,又能以唐人为规范,成以后人所总结的欧阳询“三十六法”更具经典的意义。“三十六法”名目繁多,而归根到底,便是最后的“恰好”一法,也就是要求使每一个字的点画疏密,形体态势恰到好处。平衡中有变化,对比中见统一。所以,一方面要恪守规矩,另一方面又不能死守规矩,而必须在规矩的基础上做到神妙变化。
三、章法
章法又称布局,是指一篇书法作品通篇的结构体势,所以又称“置阵布势”。结体是指一个字的不同点画之间要互有呼应;章法则是指一篇之中,字与字之间,行与行之间,要互有呼应。其方法大体上有四种。一种是字字独立、行行竖直、层层横平的规整章法。如小篆、汉隶、魏书、唐楷,多用这样的章法。其优点是疏朗而又分明,整齐而又森严。缺点是容易沦于状如操作数的刻板。所以,一般在总体的规整中,在个别的地方加以破解。一种是纵向贯气法。行距宽而字距紧,注重行行竖直,而层层必不横平,至于字与字之间,可独立,也可不独立。一般行书、小草书多用此法。一种是横向贯气法。行距紧而字距宽,注重层层横平,而忽略了它的行行竖直、字字独立。这种章法,就是受近代图书出版的横排版式启示而来的,一般适合于篆书、隶书、楷书,如近人陆维钊的书法便是如此来谋篇的。一种是通篇布局法。一般适合于大草、狂草书,横不见层,纵不见行,字与字之间不仅上下牵连,而且左右纠缠,纵横散乱,满纸烟云,而自成一片化机。
不同的章法,不仅与书体有关,也与书法的功能、形制有关。用于祭祀、记功、奏章、陈事等,以规整的章法最为一目了然。用于清逸的主观意兴的发抒,以纵向贯气法更为潇洒流便。用于郁勃的主观意兴发抒,从以通篇考虑的章法更为淋漓尽致。从形制而言,册页适合于规整章法,纵长的条幅适合于纵向贯气的章法,而手卷适合于通篇考虑的章法。
四、从有法到无法
从笔法、结体到章法,它们有规定的基本要求,但按部就班,还称不上是真正的书法。必须通过长期的训练,用主观的心灵去领悟,去变化,在规矩的基础上获得超升,从有法的必然王国,进入无法的自在王国,也就是由技,进入到道,这才是眉睫法艺术的最高境界。但它与胡涂乱抹并不是同一回事。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天国,是自由的驰骋于必然王国之中,又称作“给心所欲不逾矩”。而胡涂乱抹则是绕开必然王国,自由地驰骋于必然王国之外,不妨称作“纵心所欲不要矩”。
六、神 妙 能 逸
书法艺术的欣赏又称“品藻”。当“品”作为一个名词时,它是指品格、品类、品级;当“品”作为一个动时,它是指无法量化而只能意会的品尝、品。对于书法的欣赏,品尝、品是指它的方法和过程,而品格、品类、品级则是欣赏的结论。
作为书品的结论,最早时仅作上、中、下三品的分等。稍后,每品之中又各分上、中、下,遂为九等。这样的岔口,仅涉及水平的高下,而没有涉及风格的不同。从唐代以后,对书法的分品,开始涉及到风格的不同,有神、妙、能、逸、佳、高、精以及正宗、大家、名家、正源、旁源等不同的分类。而今天,神、妙、能、逸的分品,最早就是由唐代的张怀提出来的,四者之间互相平行,每品之间又分上、中、下三等,三者之间各不平等。嗣后朱景玄用这四品来评画,至北宋黄休复又在《益州名画录》中明确地分别四品不同的风格特色,认为:
画之逸格,最难其俦,拙规矩于方圆,鄙精研于彩绘,笔简形具,得之自然,莫可楷模,出于意表,故目之逸格尔。
大凡画艺,应物象形,其天机迥高,思与神合,创意立体,妙合化权,非谓开厨已走,拔壁而飞,故目之神格尔。
画之于人,各有本性,笔精墨妙,不知所然,若投刃于解牛,类运斤于斫鼻,自心付手,曲尽率微,故目之妙格尔。
画有性周动植,学侔天动,乃至结岳融川,潜翔羽,形象生动者,故目之 能格尔。
一般借鉴画品的方法,也把书品分为神、妙、能、逸四品,但是,对于四品的具体解释,不定还是未能取得统一的认识。因为,书品,无论神品她好,妙品也好,还是能品也好,逸品也好,都包含了品格(风格)和品位(等级)两个方面。这个两个方面,既互相关联,又各有不同的含义,如果把它们混淆了,难免导致欣赏时的无所适从,或不知所云。例如,同样对于“逸品”,有时从等级上去认识它,把它置于最高的品位;有时又从风格上去认识它,把它作为逸出书法正常规矩的格外一法,教外别传。这无法不使欣赏者有茫然的感觉。
在此,我们不妨借鉴四方艺术美学关于优美、壮美(在中国传统的审美分类中可以阴柔美、阳刚美与之相对应)的两分法,把逸品、妙品归属于优美的范畴。逸品不妨看做优美的极致,而中央电视台可以看做一般水平的优美;礼品不妨看做壮美的极致,而能品则可以看做一般水平的壮美。清代的姚姬传曾论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既可以用来评文,同样可以用来品书。他说:
其得于阳与刚之美者,则其文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决大川,如奔骐骥;其光也,如果日,如火,如金欠;其于人也,如冯高视远,如君而朝万众,如鼓万勇士而战之。
其得于阴与柔之美者,则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涧,如沦如漾,如珠玉之辉,如鸿鹄之鸣而入寥廓;其于人也,乎其如叹,邈乎其如有思,暖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
不过,他又认为,这两种美不是决然对立的,而总是“糅而偏胜”的。如果“一有一绝无”,那就“刚不足为刚,柔不足为柔,皆不可以言文”。而文风、书风之所以会有阳刚、阴柔之分,既有社会的原因,更关系到文学家、书法家天生的秉性、气质、才情,就像每一个人的血型不同一样。
逸品为优美品格的最高品位,如王羲之、王献之、虞世南、褚逐良、蔡襄、赵孟、董其昌、沈尹默等,功力与才情并臻胜境,而表现为清新流丽的格调。
妙品为优美品格的次高品位,如文徵明、唐寅、姜宸英、笪重光、梁同书、王文治、白蕉等,或功力稍逊,或才情稍逊(更多的是功力稍逊),而同样倾向于清新流丽的格调。其中,个别的书家,单刀直入,也有可能晋级最高的品位。
神品为半美品格的最高品位,如颜真卿、柳公权、黄庭坚、张瑞图、王铎、吴昌硕、于右任等,以功力与才情并臻胜境,而表现为浑厚端庄的格调。
能品为壮美品格的次高品位,如赵构、张即之、张照、钱沣、张裕钊、邓散木等,或功力稍逊,或才情稍逊(更多的是功力稍逊),崦同样于浑厚端严的格调。其中,个别的的书家单刀直入,同样有可能晋级最高的品位。
这样的分品,也可用于金石碑版的欣赏。如《曹全碑》、《张墨女》、《董美人》等等,均可归于优美的逸品或妙品;而《石鼓文》、《石门颂》、《郑文公》等等,均可归于壮美的神品或能品。
当然,任何分品,都只能最相对的,而不能是绝对的。如欧阳询、苏轼的书风,便介于优美与壮美、逸品与神品之间。高、次两等的分别,更是如此,如王羲之、赵孟、沈尹默,他们的等第,各有分别;颜真卿,黄庭坚、吴昌硕的等第,也颇为悬殊。
简而言之,逸品,是指优美风格中借助于功力使才情清超脱俗的一种;清超而未能脱俗,便是妙品。从总体来看,在等级上,逸品自然高于妙品,而具体的情况下,论水平不论风格的脱俗与否,有些妙品也未尝不能高于有些逸品。同样,神品,是指壮美风格中,借助于才情使功力出神入化的一种。出神而未能入化,便是能品。从总体来看,在等级上,神品自然高于能品,而具体的情况下,论水平不论风格的入化与否,有些能品也未尝不能高于有些神品。
那么,逸品和神品,作为风格而不是等级,二是是否有孰高孰低之分呢?通常认为,不同的风格是没有高代之分的,就像体育竞技中的跳高和跳远,不能说孰高孰低,而要看在各自的项目中有否拿到金牌。
但是也有人认为,不同的风格是平行而不平等的,就像体育竞技中的乒乓球和足球,足球的银牌,其价格甚至高于乒乓球的金牌。反映在文学史上,杜甫是史诗派的代表,王维是神韵派的代表,不同的风格,其比较的结果是大家公认为杜是伟大的诗人——“诗圣”,而王中介“大诗人中的小诗人”。反映在绘画史上,以王维为代表的“南宗”画风,也被认为高于以吴道子为代表的“北宗”画风。同理,在书法史上,以帖学为代表的优美的逸品书风,当然也被认为高于以碑学为代表的壮美的神品书风。至于每一个具体的书家,其个人的成就高低当然又是另一回事。
七、题 跋 歌 咏
前面所谈的书法欣赏,所欣赏的对象,可以是美术馆、博物馆中的陈列品,也可以是画册中的印刷品,当然并不排除自己或朋友所有的真迹原作。但它们的欣赏,无论立场、角度、方法是怎样的不同,共同的一点是只能用眼睛去观看,用心灵去体会。而“题跋歌咏”作为一种书法的欣赏方法,所欣赏的对象,必须是真迹原作,它可以是自己所有的,也可以是朋友所藏的,通过眼睛的观看,心灵的体会,进而还须把所得印象用自己的手组织成优美的文字并以精美的书法在作品上(一般是裱件的适当部位)书写出来。对于书法的欣赏,一量能进入题跋歌咏的层次,便标志着欣赏者进入了较高的层次,不仅入门了,并且登堂入。
一般的欣赏,只能使欣赏者从精神上受益,获得陶冶、提升,而题跋歌咏,进而还能使被欣赏的作品从价值上得以增进。
题跋歌咏的文字内容,不久乎表扬它的美,鉴定它的真。如诠释诗文、引申意境、记述作品的创作经过、评述作品的风格创造、讨论作品的技法特点,进而引证书史、阐发书论乃至感叹人生等等,凡侧重于作品可能给观赏者带来玩赏价值的,均属于表扬其美的范畴。而考订诗文的故实制度、分析作品的风格技法、探讨作品的庋藏留传——包括购藏作品的经过及价格,进而鉴定作品的真实可靠等等。凡侧重于作品可能给收藏者带来玩赏、收藏价值的,均属于鉴定其真的范畴。文字可用文言的诗文,一般不用白话,庶使其显得典雅。有时,也可以用图画的形象作为题跋。
在这方面,要求题跋者具有清隽的诗情文才,作得一手好诗、好文章,其次才是懂得书法。从历代书法鉴赏的题跋歌咏文字来看,包括直到今天,许多文人、大学中评议系的教授所做的鉴赏文章,水平更在书法家、书法鉴藏家之上。勉强去题跋歌咏,不仅不能提升书法欣赏的品位,反而成为佛头着粪。例如清代的乾隆皇帝弘历,在这方面便被作为反面的教材。自然,正面的教材应该是宋代的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等。
题跋歌咏的书法形式,一般用于端正的行、楷书,而少用篆、隶、狂草书。字形以小为主,但手卷的引首,也可用大字形的篆、隶书。在这方面,对于题跋者的要求,是能够写一手工整且漂亮的字,而不一定擅长书法。我们看历代书法世迹上所留下的题跋,许多人并不擅长书法,甚至在书法史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名头,但因为他的字写得非常认真,所以不失为好题跋。而如吴昌硕、齐白石等,书法的水平当然非常高,但他们狂野的书风,却不适合用于为一件书法名作鉴赏题跋,原因便在于此。
题跋的位置,视作品的装裱形制而定。一般挂轴题于诗塘、裱边;手卷题于引首、拖尾、隔水;册页题于前后副页。而不论何种形制,签条都是需要题签的,但只题作品的名称,包括它的作者。
除了歌咏题跋外,还可以在作品的适当部位铃盖鉴赏印。其印文的内容,不久欣赏姓名字号下缀“过目”、“清玩”、“眼福”、“审定”等字样,也可用表明欣赏者品操志趣的“闲章”。而印风,无论朱、白,一律以工整的形式为宜。当一件书法名作,为我所拥有,由我自己或请朋友在其上题跋歌咏,这种欣赏的方式比单纯的欣赏,自然更增加了乐趣,也使欣赏得以深化化,使欣赏水平得以提高。当一件书法名作经过许多人的题跋歌咏,有三两知己来家做客,把它拿出来共同欣赏,一段一段地展开,品读作品本身,品读题跋。作品的诗文的是好诗文,书法是好书法;题跋的诗文同样是好诗文,书法同样是好书法,题跋与作品相互辉映,如众星捧月、绿叶扶花,那更是怎样一种高雅的生活情趣啊!
八、结 语
同一件书法作品的欣赏,固然有多种多样的方法,可使欣赏者获得多种多种的益处。而同一位欣赏者,即使使用同一种方法来远行欣赏,因所欣赏的作品各不相同,所以同样可以有多种多样的收益。自古以来,把书画的欣赏比作“特健药”、“清凉散”,意味着通过不同作品的欣赏,可使欣赏者从精神品操上却病延年,达到身心的健康。这是非常有道理的。因此,书法欣赏,不仅注意欣赏的方法,根据各人的不同特点而有不同的侧重,还要注意欣赏的对象,根据各人的不同需要有不同的侧重和选择,庶几对症下药,事半功倍。
清代的张潮,曾写过一篇《书本草》,以经史子集、道释传奇比作不同的药物,在此,我们不妨也开一张书法的“本草”方子:
二五、欧诸虞恭颜柳、苏黄米蔡、赵孟、董其昌,如“四书”、“五经”,俱性平味甘无毒,或有略苦微毒者,服之清心益智,或有略苦微毒者,服之清心益智,寡嗜欲,久服令人面盎背,心广体胖。
三代秦汉金石碑版,如“诸史”,味或有带甘者,而大多苦涩,服之增长见识,有时令人怒不可解,或泣下不止,当暂停,复缓缓服之。但此药价昂,无力之家往往不能得,即胜不易,须先服“四书”、“五比”,再服此药方妙。必穷年累月,方可服尽,不可因其似旦夕奏功而以为真旦夕所能奏功。官料为上,野者为,不堪用,服时得酒为佳。
张旭、怀素、杨维桢、祝允明、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王铎、傅山、八大、石涛,如“诸子”,性寒带燥,味有甘者、辛者、淡者、烈者,俱有毒,可攻窒滞,然须慎服,不慎,至今人狂易。
扬州八怪、嘉道后碑学诸家,如“诸集”,性味不一,俱有毒,服之助气,亦能镶,须择其佳者方可用,否具杀人。
魏晋墓志造像,如“释典道藏”,性大寒,叶苦烈,有毒,平素不可服,服之令人身心俱冷。唯热中者宜用,胸有磊块者,服之亦能消导。忌酒,与茶相宜。
“民间书法”,如“小说传奇”,味甘性燥,有大毒,不可服,服之令人狂易。唯暑月神气疲倦,或饱闷后,风雨作恶,及有外感者,服之解烦消郁,释滞宽胸,然不宜久服也。
这几段文字,基本是仿袭张潮的《书本草》。其中的模拟及对于药性和效用的分析,不一定十分准确,但它的目的,只是为了说明这样一个问题:欣赏,关系到欣赏者和被欣赏的对象两个方面,缺少了任一方面,欣赏便无法成立;这两个方面不能契合,欣赏同样不能成立。
欣赏的目的,既是为了思想境界的提升,精神情操的陶冶,那么,当他尚水进入欣赏之前,其思想境界、精神情操必有所欠缺和不足。这欠缺和不足,便是“病”。现在,便要通过书法的欣赏,把这“病”祛除掉,使身心由不适变为健康,健康而更健康。
无疑,不同的欣赏者,当他尚未进入欣赏之前,所患的身心上的“病”是各不相同的,自然,出于对症下药,他所应该或需要欣赏的作品,也应该是各有不同的。毫无疑问,生理上的病与身心上的“病”有不同的性质,为了医治生理上的病,所使用的药必须是严格对症的,而为了医治身心上的“病”,所使用的药去不需要严格对症。所以,所谓的“书本草”,无论对于诗文的“书”,还是书法的“书”,都只是大体上的,而且是理论上的,而不是具体地来规定谁应该或只能什么样的书法作品进行欣赏。
在通常的情况下,身心上的“病”也可以看做一种“需要”。任何一个人,身心上的需要是多样的,而不是只有一种或少几种。他既需要恬淡,也需要刺激,既需要婉约,也需要豪迈……自然,无论是什么样的书法作品,对他来说,都是可能开卷有益的。但是,在特殊的情况下,当一个人的秉性是暴躁的,而且又遇上了不顺心的事时,对他来说,为使暴躁的心情趋于冷静,更适宜的当然是王羲之的《兰亭序》,而不是怀素的《自叙帖》。而当一个人的秉性是内敛的,而且正需要他在工作上去打开局面时,对他来说,为使内敛的性格转向开拓,更适宜欣赏的当然是黄庭坚的《松风阁诗》,而不是赵孟的《汲黯传》。当然,这一切,都是潜移默化的,而不可能是药到病除的。
 爱华网
爱华网